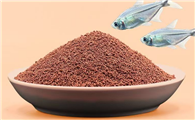非人类的动物能够思考吗?如果能,它们能想到什么?狗可能会相信某些事,会有某种欲望,但它们会设想事情的可能性吗?比如,考虑或希望某件事可能会怎么样?无论非人类的动物能不能进行某种类型的思考,有件事很明显,人类的认知能力与其他物种的认知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差距呢?我们可以用动物和人类之间最明显的不同——是否拥有自然语言——这一点来完全解释这种差距吗?还是说,还有些非语言因素起了作用,也会造成我们和其他物种之间认知能力的差距?这些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引起了争论,直到今天,这些争论仍在继续。

初步挑战
只要涉及动物思维的研究,一开始就会面临不少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动物是否可能拥有思维能力。关于动物的思维能力这件事,究竟是一个开放问题,可以用正常的科学手段来找出答案,还是像很多理论学家认为的那样,存在某些根本性的原则,使得没有语言的生物根本就无法思考?
为了证明必须有语言才能思考,最明显的策略就是论证语言和某种认知能力密切相关,而这种认知能力正是思考所必需的。例如,在看不到物体的情况下表征物体的能力,表征各种物体及其属性的能力,或者以一种系统的、开放的方式描绘一个人所处的周边环境的能力。这些能力都需要掌握自然语言才能拥有吗?当然,如果说自然语言可能会促进这些能力的掌握,这肯定没错。事实上,在认知结构上甚至可能存在某些生物学上的限制,从而阻止生物获得这些认知能力。比如,对某些认知能力,如果一个生物没有首先(或者同时)学会语言,就无法获得。尽管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做出过断言,但并没有很好的先天证据证明,必须掌握一种公共语言才能获得这些能力。思维能力确实需要某种形式的表征系统,但这个系统是不是必须采用自然语言的形式,或者说,它会不会是与“思维语言”类似的系统,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二个挑战则是关于方法的挑战:即使那些不会说话的生物能够思考,我们又怎么能在这些生物身上发现思考的证据呢?如果一个生物不能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怎么能确定它思考的内容呢?我们又怎么能确定它真的在思考呢?
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类认知问题也面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挑战,也就是认为只有能够回答我们问题的生物才具有思维能力。正如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疯帽匠对爱丽丝说的那样,我们说的并不总是我们想的,而我们想的也并不总是我们说的。对语言的解读通常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我们要依靠大量的背景假设,例如要知道说话的人是否真诚,是否了解听众,是否清楚自己所用词汇的意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他说的话里推断出他的想法是什么。此外,虽然非语言生物无法告诉我们它在想什么,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它在想什么。例如,我们可以观察生物对不同道具表现出来的不同敏感程度,由此做出判断。假设我们想知道狗能否想到松鼠;如果狗能在周围的环境中认出松鼠,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狗可以想到松鼠。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比方说,这条狗相信树上有一只松鼠。(当然,我们不必要求狗能够把松鼠和其他所有东西区分开来,然后才说它的确想到了松鼠。毕竟,我们自己也无法把松鼠和某种像松鼠的仿真物区分开来,但我们毫无疑问可以想到松鼠。)可以说,在证明思维能力方面,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只是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区别。
因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断然否定非语言生物具有思维能力的可能性,同样也没有理由假设我们无法检测它们可能具有的思维能力。比起没有语言的生物,语言可以使我们更精确地了解一种生物的思想;但如果因此认为我们永远无法了解非语言生物的思想,那就错了。
数学、社会学和心理学
我们该到哪里才能找到某个物种具有思维能力的证据呢?我们可以考察它的导航能力,因为导航能力往往需要以复杂的、系统化的方式描绘身边环境的时间和空间特征。或者,我们还可以考察它制造工具的能力,因为把一个物体制造成工具,需要掌握这个物体的因果属性。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我们在这里将集中在三个领域寻找非语言生物具有思维的证据:数学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及心理学领域。
研究表明,许多物种能够跟踪所处环境中物体的数学特性。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罗素·丘奇(Russell Church)和沃伦·梅克(Warren Meck)把老鼠放在一个实验环境中,它们可以听到声音,看到闪光。这些老鼠在实验之前受过训练,听到两次声音就拨动左边的控制杆,听到四次声音就拨动右边的控制杆。此外,这些老鼠看到两次闪光就拨动左边的控制杆,看到四次闪光就拨动右边的控制杆。那么,当老鼠听到一次声音并且看到一次闪光时,会做什么呢?它们会立即拨动左边的控制杆,这表明它们已经将这种刺激编码为“两个事件”。同时,听到两次声音并且看到两次闪光后,它们会立即拨动右边的控制杆,表明它们已经将这种刺激编码为“四个事件”。
有些物种能够比较数量的多少,而且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灵长类动物学家杜安·蓝保(Duane Rumbaugh)和他的同事向黑猩猩展示两盘巧克力饼干,但它们只能选择一盘。每个盘子里都放了两堆巧克力饼干。例如,在一个盘子里,可能一堆是三块巧克力饼干,另一堆是四块巧克力饼干;而另一个盘子里,可能一堆是七块巧克力饼干,另一堆是两块巧克力饼干。黑猩猩很喜欢吃巧克力饼干,所以它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要确定哪个盘子里的饼干数量更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黑猩猩首先要把盘子上的两堆巧克力饼干相加,然后算出哪个盘子里的饼干更多。尽管当两个盘子里的饼干数量非常接近时,黑猩猩会犹豫,但它们一般会很精确地选择装巧克力饼干更多的盘子。
事实上,有证据表明,黑猩猩甚至能掌握简单的分数。在一项实验中,灵长类动物学家戴维·普雷马克(David Premack)和盖伊·伍德拉夫(Guy Woodruff)训练黑猩猩识别半个物体。例如,当黑猩猩看到半杯牛奶时,它们会选择半个苹果而不是四分之三个苹果。然后,普雷马克和伍德拉夫让黑猩猩看一张四分之一个苹果和半杯牛奶的图片。这些动物能够将这两幅图像结合起来,并把它与代表四分之三的图像匹配起来。这表明,它们对分数有直观的理解。
总的来说,证据表明许多物种——甚至包括六个月大的人类婴儿——都能精确地表征较小的数(1、2、3以及比3大一点的数),也都能以近似的方式表征较大的数(也就是超过3的数)。这种表征能力,是一种类似思维的能力;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能力都与接收到的刺激无关。然而,无论是非人类的动物还是人类的婴儿,似乎都不能精确地表征更大的数字。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这种能力可能需要掌握数字的写法。
现在让我们转到第二个领域,即社会关系领域,看看我们已经获得哪些证据,证明动物具有思维能力。在许多物种中,社会地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个体不仅要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且要能识别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社会地位;这一点至关重要。灵长类动物学家多萝西·切尼(Dorothy Cheney)和罗伯特·赛法思(Robert Seyfarth)以狒狒作为研究对象,对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认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每只雌性狒狒在整个族群中的社交关系包括了两层等级制度:狒狒所属的整个家庭在族群社会中有相应的等级地位,雌性狒狒在家庭内部也有相应的等级地位。这些等级地位是会变动的,并且在构建狒狒与族群其他成员的互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当我们发现狒狒对它们的社会有一套复杂的表征系统时,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当狒狒听到来自低等级家庭威胁高等级家庭的一系列叫声时,会比听到来自家庭内部的类似叫声更为惊讶;甚至当这种威胁来自与它们同等级的家庭时,更是如此。
狒狒对社会的理解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思维的特征。首先,狒狒对自己社会的理解与任何特定的知觉模式并无关联,而是独立于它们的直接知觉环境的。例如,一只狒狒发出一系列声音,而另一只狒狒在解读时,可能既要取决于它听到的声音,也取决于它看到的情景。其次,狒狒关注的这些属性(比如从属地位)并不直接体现在动物的生活环境中,而是需要运用一套理论,通过观察一只狒狒的生理特征和行为特征来判断它的社会地位。一个不懂这种理论的人,就没办法像狒狒那样了解群体中各个成员间的社会关系。再次,狒狒对其社会环境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似乎是系统化的、开放的。狒狒可以表征部落成员之间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它不但能表征那些它意料之中的关系,还可以表征那些出乎意料的、不协调的关系。综上所述,这些特点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证据,证明我们可以把狒狒对自己社会的表征行为描述成一种思考能力。
我们可以把某些非人类的物种看成业余社会学家,但它们也有资格成为业余心理学家吗?我们人类拥有复杂的能力,可以辨识自己和他人的心智状态,但其他物种也有这种能力吗?

关于这些心智能力,让我们先从一个相当基础的方面说起:视觉。动物看到其他生物注视某个方向,能基于这个信息看出——或许是知道——某些事情吗?至少,灵长类动物似乎对“看到”和“知道”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例如,灵长类动物会顺着另一只动物的目光看去,来确定对方正在注意什么;它们还会把珍贵的食物挪到远离其他动物视线的地方。但是,灵长类动物真的能理解视觉的概念吗?还是说,它们仅仅知道和视觉关联的行为,比如知道动物看到心仪的食物就会吃掉它?
灵长类动物学家丹尼尔·波维内利(Daniel Povinelli)和蒂莫西·埃迪(Timothy Eddy)开展的一系列实验表明,黑猩猩似乎只把视觉当作一种“看”的行为。在这些实验中,黑猩猩可以选择向两个人中的一个人乞讨食物。其中一个人能看到黑猩猩,而另一个人尽管面对黑猩猩,却看不见它;要么是因为她头上套着水桶,要么是因为她戴着眼罩(参见图)。波维内利和埃迪发现,黑猩猩并没有表现出更愿意向看得见它的人乞讨食物,这说明黑猩猩并不理解“看到”和“知道”之间的联系。